[编剧] 编剧们写剧本得流血、流汗也流泪
2015-02-27 17:16:59
来源:天涯论坛[摘要]芦苇是个和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初次见面,他在北京东北四环外的一座别墅中和人讨论剧本。正值炎夏,他一身白色,T恤、棉布长裤,配一双老头布鞋,夹坐在一桌人中间的他瘦瘦高高,霎是显眼。到了饭点,别人都吃饭,主人为他单煮了一大碗白面条,他捧着碗,吃得挺香。
别墅的主人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人,操一口南方口音普通话,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一模一样的硬壳精装礼品书。时不时过来和芦苇搭两句话:“芦老师,你可千万别上时尚杂志封面啊。”
“嗨”,芦苇摇摇头,“你见过哪个编剧上杂志封面的?不可能。”
做电影编剧26年,芦苇已经习惯了寂寞。大多数时候,编剧是个手艺人,埋头做活儿的他不停在写,能拍成电影的却是少数。如果单看记录,甚至有点尴尬——除却还在拍摄,将于明年上映的电影《狼图腾》,由芦苇担任主要编剧的电影,最近一部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图雅的婚事》,再上一部作品则是更遥远的1997年,他自编自导的电影《西夏路迢迢》。
不是没有大制作电影找上门来,吴宇森的《赤壁》因两人争论是否应设置小乔刺杀曹操导致不欢而散,吴宇森最终完全弃用芦苇写好的剧本;王全安的《白鹿原》采用了芦苇剧本中的一部分,剧本逻辑与情节设置仍遵循王个人意志。看完电影后,芦苇称,这部电影与自己完全无关。
这次与《狼图腾》导演让雅克阿诺合作,芦苇说,“阿诺是个正常人。”末了又补充一句,“你跟中国导演接触,一个个心里头都不大正常。”
多少有些诡异,身为中国最好的编剧之一,他曾和中国最杰出的导演们亲密无间。与陈凯歌合作的《霸王别姬》、与张艺谋合作的《活着》都是经典。除此之外的《秦颂》、《黄河谣》、《红樱桃》与《疯狂的代价》等也都名噪一时。他却以近乎决绝的方式,与越来越红火的中国电影主流渐行渐远。陈凯歌在《霸王别姬》后再次请他合作《风月》,听完故事的第二天,他就要求退出,推荐了王安忆担任编剧。他说,“我一个西安人,哪知道大上海的事。”
不是没人拿着钱找芦苇,希望借他的名头,攒个本子拍戏。可他脾气倔,挑题材,也挑老板。“你让我写《致青春》,写《小时代》,我写不了。”仍住在西安的他,说自己“跟影视圈八竿子打不着”,“不认识几个圈里人”。每年只写一个剧本,接触一个老板、一个导演,还特别坚持原则——要对电影负责任,不能拿电影蒙钱。
这几年,找到他的老板总问他同一个问题,“芦老师,搞什么电影可以挣钱?”芦苇特别烦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也永远一样:“别说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了,我也绝不告诉你。我肯定自己发财,干嘛让你发财呢?”
电视剧市场红火后,有人高薪延请他编写电视剧剧本,他以“体会不到工作快乐”为由,拒绝了,还说“如果我家有隔夜粮,我就不当电视剧编剧。”
久而久之,上门的人也少了。有人说,芦苇太狂傲。芦苇鼻子里哼一声:“不是我骄傲,是烂人太多。和脑残打交道,有意义吗?你救得了他吗?”
钱钟书说过:“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芦苇背了一遍这句话,抬头问我,“我问你,荒江野老是什么意思?”然后自问自答:“就是和这些潮流有距离。”
二
芦苇本姓卢,在狂热而混乱的岁月里,他丢掉了这个名字。户口本从城市到下放的农村,再辗转回到城市,不知哪个环节上出了错,他从此成了“芦苇”。
和这个名字一样,芦苇的命运里,也充满了各种机缘巧合。
生于1950年的他,和同龄人一样将青春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当中。18岁在宝鸡农村下乡,4年后返城,他成了无业青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西影厂招收炊事员,26岁还无所事事的他被街道办安排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又因为爱好画画,被调到了美工岗位,自此与电影结缘。
动荡的岁月里,他一直坚持读书。没有书,就偷。从各家抄缴来的书当时全堆放在学校操场上,每到夜深人静,他就拿几本回家。图书馆被贴了封条,他和朋友一起用起子撬开窗户,翻进去找书。
文革后期,他开始对社会现实产生怀疑。“人活着得有信仰,可我们相信谁呢?”无业青年芦苇发出了这样的诘问。他与十余名同样苦闷的知识青年结成了秘密学习小组,重新研读共产主义经典理论著作,试图从中寻找思想出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与新华人寿董事长康典,也都是这一小组成员。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他社会学基础理论丛书都成为了他们的学习素材。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举报,小组每两周聚会一次,时长五六个小时,每次都换地点。学饿了,众人就凑钱一起上街吃碗面、啃个馒头,继续讨论。整整持续了三年时间,文革结束,小组才告解散。
进入西影厂的芦苇,常与其他年轻人玩在一起。好友周晓文初做导演,拿到的剧本《他们正年轻》不够成熟,芦苇边看边骂,周晓文激他,“你觉得不行,那什么行?”芦苇说:“我写的起码比这个好。”还是美工的他就真把剧本拿回了家,白天做美工,晚上改剧本。改着改着,索性自己也写起了剧本。
没学过任何系统电影理论的芦苇,编剧老师是一本双月刊杂志:《世界电影》。每期都刊登一部经典电影剧本。芦苇收集了他能找到的每一期。在看不到太多电影的时代,他依靠这本杂志接触到了许多杰出国外电影。他尊称黑泽明为“真正的老师”,在他还从未看过《七武士》时,他就已通读了多遍《七武士》剧本,并从中收获良多。
芦苇的侄子如今与他住在一起,学做编剧。进门的第二天,他扔给侄子一本书,《黑泽明传》,要求他在学习前读完。侄子说起读后感,“水平是一码事,态度又是一码事。黑泽明的一生恰应了一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
芦苇教侄子的第一课,不是电影理论,而是拓剧本。他要求侄子一遍遍地看《阿拉伯的劳伦斯》,想象自己是编剧,如何由电影反写出一个剧本。
这也是他当年的学习方法。七十年代末期,西安举办美国电影周,科波拉的《黑狗》上映了一周,他每天都自费去看一场,回家就做一篇笔记。电影票价一张三毛钱,而他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十六块钱。
他为所有当年看过的电影都做了笔记。从剧本特点、导演特点、表演、演员和音乐五个基本要素分析。时间长了,他变得敏锐起来,看电影先看类型。“类型就是电影的规定性。它不能成全你,但是它可以保证你不犯基本错误。”他说自己编剧时,“不管写什么电影,首先面对的就是类型。到底要写一个什么电影,要有一个定位。说白了,就是知道观众要看什么。类型是一个工具,它让你明确写剧本时必须具备的特点和材料。比如,剧本属于爱情片类型,里面却没有爱情,那这个电影到底在说什么?”
观众对主旋律片、战争片、爱情片与警匪片的期待是不同的,编剧有必要满足观众的期待。“我是个凡人,所以不大做梦,类型翻新是天才干的事。”
三
芦苇说,自己是中国最早写类型片的编剧。与周晓文合作的两部电影《疯狂的代价》与《最后的疯狂》是中国最早的警匪片,取得了票房与口碑双丰收。陈凯歌也
正是在看过这两部电影后,找到了他,邀请他合作《霸王别姬》。
二十年过去后,芦苇说,“《霸王别姬》就是我理想中的中国电影创作状态,再没有比那个更好的了。”
他信奉左宗棠的战术“缓进速战”,准备得扎扎实实。“剧本不是拿手写出来的,而是拿脚写出来的。”接下《霸王别姬》后,他索性住进了北京图书馆旁边的招待所,每天在里面研读近代戏曲与历史材料。中央戏曲学院图书馆与戏曲家协会数据室的工作人员也成了他的朋友,帮着他收集材料。梅兰芳、齐如山、袁世海、叶盛长、侯少奎的材料、书籍,他个个如数家珍。
为了写剧本时有京腔,贴合人物性格。芦苇从陈凯歌父亲处借了盘《茶馆》的录像带,每天跟着学,用京腔与人对话,他后来背过了《茶馆》60%以上的台词。
他为剧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写了人物小传。程蝶衣一角,他写了五页纸,陈凯歌也写了三页。
筹备《霸王别姬》时,陈凯歌新作《边走边唱》正要上映,芦苇与李碧华一同观看,李说:“我是边看边睡。”陈凯歌将电影诗意化、去剧情化的倾向在这部电影中愈发明显,票房失利。芦苇劝他,放弃过去的理念,用好莱坞经典模式、经典架构,完整拍一部讲故事的电影,也就是《霸王别姬》。陈凯歌做出了妥协。同时,一向喜欢自己参与剧本创作的陈凯歌也充分尊重芦苇,只按场次标出上、中、下,上即满意,中可切磋,下则需要修改。他并未亲自动手。两人的讨论过程也非常愉快,芦苇说,“就像运动员,越是遇到劲敌,越能激发动力。”
初稿写到一半时,陈凯歌问芦苇,“写的怎么样了?”芦苇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听完后,陈凯歌笑得很灿烂,他说:“吃饭,吃饭,咱们的戏有根了。”
剧本后来写了两稿即定稿,芦苇一到北京,陈凯歌就紧紧拥抱了他。后来,反倒是芦苇追着陈凯歌,要求再修改一下剧本的后半部分。这部戏,芦苇共写了99场,时长2小时45分钟。
不仅是剧本部分,陈凯歌尊重芦苇的意见,在选角时,陈凯歌也做出了妥协。程蝶衣一角本意属当时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名的尊龙,但看过《胭脂扣》的芦苇则倾向于张国荣。剧组包括摄影师顾长卫、执行导演张进战、录音师陶经和陈芦在内的五人投票,最终结果四比一,只有陈凯歌投给了尊龙。陈凯歌说:“我什么都不说了,就张国荣。”陈凯歌对《霸王别姬》服装不满意,也叫来芦苇,让他在剧本反面的白纸上画出服装样式。服装师听不明白,芦苇建议陈凯歌换人,陈想了想,照做了。芦苇说,“那时我们是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说,直来直去。我们的合作简单、利索、直奔主题,每个人都把自己最优秀的东西激发出来了。”
电影成片后,剧本、摄影、美术、服装、道具都均收获赞誉,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被公认为是陈凯歌电影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1994年,这部电影在国内禁止宣传的气氛中低调上映。在当时电影院只有两千家(截止2013年底我国有超过14000家电影院)、一张电影票只有4元钱的情况下,当年收获约四千五百万票房。同比换算,相当于如今的8亿元票房。
芦苇说:“《霸王别姬》证明了一件事,挣钱可以不下三滥,也可以站着把钱挣了。”随后他感叹:“陈凯歌要是能保持《霸王别姬》那时候的状态,到今天,中国的艺术电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
他和陈凯歌与张艺谋都已经断了来往,而且并不讳言对今日两人的批评。“闪亮登场,后戏无力。往大里说,这是民族性问题,我们中国人有个通病,早衰。”
陈凯歌邀他参与《风月》,他拒绝了,表面的原因是不熟悉上海,实则是觉得陈“假大空”,“电影是人状态的产物”,他说。
陈凯歌筹拍《荆轲刺秦王》时,曾邀请过张艺谋饰演秦始皇。一开始,张艺谋答应了,却在与陈讨论剧本时遇到了问题。他告诉芦苇,“我听不懂凯歌要什么,他把
角色讲得云里雾里。”芦苇说,张艺谋遇到了自己后来与陈凯歌合作时同样的问题,“他把自己凌驾到了电影之上。”
陈凯歌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自己是程蝶衣,芦苇说,“他是段小楼。他是假霸王。”然后他笑了,“挺有意思的,程蝶衣说‘你是假霸王,我是真虞姬’,这何尝不是我
自己的感叹。”
“陈凯歌和张艺谋把很大的功夫用来扮演一个角色,走不出来,已经习惯了。他们俩本质上是一样的,需要人们崇拜他们,把他们当上帝。”芦苇说。
那他自己呢?“中国电影编剧历来都是小媳妇,从来不被人重视,从来都是干活的。没有地位,没有影响力,没有发言权,这是真的。电影圈说话算数的,那是审查阶层、老板、投资者。他们有权有势,他们掌控电影的命运。我们属于打工阶层里面,有技术成分的打工者,是匠人,待遇稍微高一点,吃的好一点。但你依然是个打工者。”
四
每年都有几个月,芦苇会在全国各地采风。其余时间,他都独居在西影厂的家属楼里。我在西安见到他时,他刚从青海、阿坝和甘孜采风回来,他想写一个关于藏族医生的故事。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移居美国,他也去过,又回来了,那里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作为一个编剧,他认命了,“我只能写中国故事的话,最好还是在中国待着。”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在深圳教书的侄子放暑假时就来和他住在一起,房间里堆满了杂物。芦苇喜欢收集各种影碟、书籍和资料,有些就扔在地上。两百多张藏族歌曲CD、盒装的纪录片和一张刚刚看完没套外皮的《小时代》DVD就这么混放在一起,墙边上的碟片垒得快有天花板那么高,赵季平去他家,直感叹他的CD比自己的还多。
他家的厕所、厨房和客厅里,随处可见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杂志与资料,还有经典文学著作。角落里还放着块白板,上面写着他给《白鹿原》做的电影分场。即使拍不成心中的那部《白鹿原》了,他还是留着,做个念想。
写剧本26年,他最想拍却没拍成的两个剧本,一个是《白鹿原》,另一个是《岁月如织》。后者的原型是陕西一个农民写的日记,从建国后一直写到五十年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跨度。西影厂老厂长吴天明找到芦苇,希望他将之改成剧本。
芦苇将《农民日记》改成《岁月如织》,写了大半年,浸淫了自己的个人史。他将插队时看到的情景都融进了剧本——因为饥饿,主人公的妻子去别的生产队偷喂牲口的苜蓿,洒糠皮给孩子吃,妻子和干部丈夫起了冲突。
看过的人都说这个剧本好,他很得意。但北影厂告诉吴天明,这个剧本肯定收不回三千万投资,项目搁置了,没人知道有没有其他原因。芦苇有些伤感,但他也明白,审查因素会让每个投资者都心存顾忌。他只能宽慰自己,他在书写底层人群的真实。
一个好编剧应该怎么做?芦苇的答案是:尽量地忠实于生活。他信奉戏假情真,打动人的并非情节真实性,而是情感的真实力量。“电影要像生活中的朋友一样,面对和解决你真实的问题。你生活中遇到事情去找朋友,朋友讲又空又大的道理,你也气死了。人们到电影院来,是要寻求感情寄托和疏泄。电影无法和他们交流,人们自然会感到失望——假模假式骗谁哄谁呢?”
他能够理解《小时代》的出现,“它安慰了这么多粉丝,让他们满足、幸福与陶醉,这是郭敬明不可抹杀的社会作用。”他也认为郭敬明并不像有些电影评论家所批评的一样一无是处——《小时代》的类型清楚,要素齐全,这已让许多国产片难以望其项背。
可他也由此对电影市场和社会失望,“《小时代》最大的问题是,它品质低俗,它在骨子里崇拜金钱、成功和权势。”“郭敬明和《富春山居图》的导演孙建军,这些人应该考虑一下,你们在数钱笑的时候,这些钞票是口水淹出来的,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口水把钞票都浸透了!”
在他看来,建国后的中国电影经历了由政治化工具转化为商品工具的过程,由“伪理想主义”演变成为“拜金主义”。唯独没有得到彰显的,就是电影的文化品质与文化功能。热闹的电影市场将观看电影变成了纯粹的感官行为,没有情感与心灵的碰撞。
“电影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电影的文化素质取决于民众文化素质,文艺片在中国一直不是主流。”整个华语电影工业,唯一还在进行文化思考表达的只有台湾电影和部分香港电影。他特别喜欢《赛德克巴莱》,这部讲述台湾乡土少数民族历史的电影,在他看来,“力图坚持一种本土文化立场的表述。而在我们大陆,这已经死掉了。”
他仍然在看中国电影,只是看得越发少了,一两个月才进电影院一次,大多数时候在家看,看得老生气。他觉得《小武》不错,《三峡好人》也可以,“至少面对了真实的问题。”有个导演他特别喜欢,叫徐童,拍了四部纪录片,镜头对准的都是底层人民。退休工人、妓女、算命的残疾人和小偷。他说,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我的心在流泪。”
他多少和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着距离,冷眼旁观着沸腾的现实。这些年来,他必须一次次面对那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他是不是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了?
“你就是说我过气了,不够红了呗。”他直接戳穿了这个问题。
王全安就这么攻击过他,在《白鹿原》上映后,面对芦苇对剧本的指责。王全安说,芦苇的剧本十年拍不了一部电影,言下之意,他的意见不重要。
芦苇生气,他说:“我觉得好笑,那《图雅的婚事》剧本哪儿来的?”有人出来做和事佬,《图雅的婚事》帮助王全安拿到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让他一跃成为重要导演,说他是“踩着芦苇的肩膀向上爬”。芦苇想了想,只说:“就算没人拍我的戏,你也不能说我没有写,我没有努力,对不对。”
他觉得年过六十的自己写得比过去更好了,创作高峰过去没有,留给作品说话。体力上当然弱一点,不能像年轻时一样,六天写一个35000字的剧本。可现在速度慢了,经验却更丰富。他也相信总有人要看自己的电影,“我一点都不恐慌。那些对电影有人文诉求的人,总会来看我的电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电影,要成为一个主流电影。”
有朋友骂他,这么多年还是想不通,总是埋怨他,脑子这么聪明,当年如果下海挣钱,现在早就发财了,干嘛要“献身艺术”。他说,“我热爱这个职业——编剧这职业是一个舞台,你自己可以演那么多角色,男人女人,好人坏人。他可以幻想各种东西,各种角色,这是编剧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他偷着乐的办法。”
所以他说,“我从不写我不想写的东西。某种意义上,编剧是个拳击手,你得来真的,你得白纸黑字一场场戏交出来,你得流汗、流血也流泪。”
往前看30年,当芦苇还只是一个游手好闲又苦闷的青年,而书也还是一种稀有资源时,他常四处借书看,遇到好的就手抄留存。那时他抄过一本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的书。手抄本他一直保存至今,并要求侄子也细细研读。
在那些工整的字迹所叙述的故事里,别的海鸥每天只做一件事,低飞,东躲西闪争抢一点早饭,晃到渔船周围找点死鱼烂虾。然而,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却远离群鸥、海岸和渔船,在远方独自练习飞行。
格格不入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被它的族群所驱逐,因为飞是一种禁忌。它只能独自离开,经历了漫长的学习与自我挣扎过程后,它学会了飞行,并且返回到了那些驱逐它的海鸥族群当中,渐渐地,将它们感化,让它们也开始梦想在天空自由翱翔。
“为什么,”乔纳森弄不明白,“世界上最难的事是让一只鸟相信他是自由的呢?只要花点时间学习,他自己也可以证明的。为什么这么难办?”
合作方动态
-
 人民网人民网,创办于1997年1月1日,是世界十大...
人民网人民网,创办于1997年1月1日,是世界十大... -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以宣传电影、培养电影观众、传播影视文化...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以宣传电影、培养电影观众、传播影视文化... -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是幸福蓝...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是幸福蓝... -
 大唐辉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型都市情感话题剧《想明白了在结婚》目...
大唐辉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大型都市情感话题剧《想明白了在结婚》目... -
 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巨资打造的电视剧《楚汉争雄》,由黄秋生...
中视精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巨资打造的电视剧《楚汉争雄》,由黄秋生... -
 中视丰德影视版权公司中视丰德影视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北...
中视丰德影视版权公司中视丰德影视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北... -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由唐德影视斥资重磅打造的战争钜制《彼岸...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由唐德影视斥资重磅打造的战争钜制《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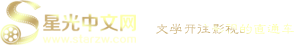

 分享
分享



 客服QQ:1055000316
客服QQ:1055000316